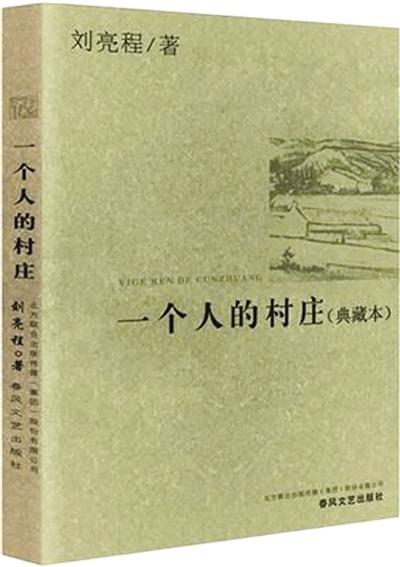
——刘亮程
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,声音承载了无形的信息,声音也表现为不同的语言。在声音里,我们听见彼此,在声音里,我们看见世界。
但你可曾想过,每种声音不同的形状?你可曾想过,每种语言所描述的天亮与天黑或许也都不一样?
近日,著名作家刘亮程书写了一本与声音有关的小说,这个历史故事亦是关于信息与语言的传达。故事发生在千年前,位于东边的毗沙国与西边的黑勒国势不两立,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。两国间书信断绝,民间捎话人由此成了一种秘密职业,承担着传递两地间信息的重要角色。小说中的捎话人库,是毗沙国著名翻译家,通数十种语言,他受托将一头小母驴谢如同“捎话”一般,从毗沙捎到黑勒。库说,我只捎话,不捎驴。委托人却说,驴也是一句话。
故事就这样开始了……
在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里,风声、驴叫、人语、炊烟、鸡鸣狗吠都在向远方传递着话语。各种语言悄无声息穿行其间,神不知鬼不觉,却神鬼俱现。小母驴谢能听见鬼魂说话,能看见所有声音的形状和颜色,懂得为人服役也懂得猜度人心。于是,一人一驴,背负着“捎话”的任务,穿越战场,跨越语言间的沙漠戈壁,见证了许多生死和不可思议之事。
这是一本在超现实路上走得很远的小说。刘亮程曾说:“这是一部无法形容的小说,也是一部也许要读很多遍才能读懂、读清楚的小说。可以说它是一部荒诞寓言小说,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惊悚童话,或许它还是一部死亡之书。”
评论家用“众生合唱,万物有灵”来总结这本书的意涵,“众是一种喧嚣,生可以理解是一种生命,合是一种互相较劲的过程,唱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;万物的万是多样繁复、丰富复杂,物可以把它理解得更丰富,不仅有人的世界,更有其他存在的世界,我们最本质上的那种存在;灵,这个小说中已经反复出现了灵世界,灵在这里不仅仅是灵魂,而是一种类似于托举人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。”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李舫说,“如果这八个字以外再加两个关键词,一个是历史,一个是战争,小说非常巧妙地把所有的时间空间打碎,按照自己的文学需要重新组合起来,给读者一种魔幻、超现实主义的感觉,用极其简单的语言,却造就了极致性的丰富。”
近日,就《捎话》这本小说,北青报记者对作家刘亮程进行了专访,除了信息、声音与语言,我们还聊了聊今天信息爆炸世界里的交流。
《捎话》的表层是写人的战争
人的交流之难和话语之困
北青报:写《捎话》这个故事是想捎话给谁呢?
刘亮程:《捎话》的表层是写人的战争,人的交流之难和话语之困。上层是驴鸣和万物的声音,一个立体的声音世界。那时的大地上,不光有人的声音,还有鸡鸣狗吠,驴的声音,尘土的声音,所有有声生命和无声生命的声音都在这本书中集体发声,众声喧哗。
这些万物的声音,后来逐渐地从人的生活中走失,现如今,这个世界只剩下人在说话。我想通过这样一本书,把时间深处那些人与其他生命的声音捎给今天的人们。
北青报:您说小说家就是捎话人,但您笔下捎话的人最后变成了毛驴,您不会担心吗?
刘亮程:在我的观念中,人的生命和驴的生命一样平凡也一样高贵,在《捎话》中所有生命都一样被平等对待。万物等同,万物有灵。
北青报:但也就像小说中说到的,有的话,是捎不到的。
刘亮程:其实好多话是捎不到的,小说中的捎话也没有捎到。即使在平常生活中,许多语言和信息也是到达不了的。永远有一些话走在路上,仅仅是走在路上,没有接话的人,没有耳朵和心灵去倾听它。那些话空空荡荡像刮过去的风一样。但是那些语言一直在走,即使捎不到也在走。其实捎话仅仅是一个开始,它并不代表话的到达和结束。
北青报:这本小说是一个寓言吗?
刘亮程:小说跟真实的历史脱节之后,便变成了一个孤悬的梦,独自存在了。这是我想写的一种文学。我想呈现那个时间远方的人和万物,他们的生死与声音。
北青报:您在小说中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。
刘亮程:我的听觉特别好,对声音也敏感。《捎话》写了人声之上的众声。那个时代的声音体系,所有声音都在朝远处传递,都在担负着捎话这样一种任务。鸡在把自己的叫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,另一个村庄鸡再接着叫,往下一个村庄传递。鸡鸣狗吠都是这样的,每一个声音都有形有色,有其意义。《捎话》完整地构造了从地上到天上的声音传递体系。
北青报:是不是因为生活的环境,让您对声音非常敏感?
刘亮程:我生活在新疆,地域比较宽阔。有时候人的声音传不出去的——你在戈壁滩上,或在空旷的沙漠中喊一个人,你明明看到人在前面,你的声音到达不了,因为在那样的空旷中声音是往上走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,如果在山谷中声音朝远处走,会有回音,而在那样空旷中声音是朝天上走,你随便喊出一声被天吸走了。但是更多的时候你又能听到远处的声音,因为大地太空,太寂静,只要你认真听,很远处的声音都能被风声带过来。
北青报:您每次来北京,觉得吵吗?
刘亮程:不吵,我年纪大了,耳朵有点背了。
北青报:您会不会觉得,大都市因为太喧哗,反而听不见很多声音了。
刘亮程:不是听不见,你时时听到的是人与机器的嘈杂之声。像新疆或者西域那样的地方,你能单独地听到一种声音,把这种声音辨别出来,而且刻骨铭心。因为人声本来就稀少,人声夹杂着风声中,夹杂在那片土地上其他动物的声音,夹杂在风吹过大地的草木尘土的声音中,所有的声音都会单独地被听见、被呈现,而且,每一种声音都有自己的形状和颜色。这也是《捎话》这本书所呈现的,人的声音之上还有那么多的声音,有形状有颜色,在人的灵魂之外还有那么多的鬼魂在天地间升沉、暗默、睡着醒来,那是一个声音和灵魂的世界。
北青报:不同形状的声音,能在大地上相互对话吗?
刘亮程:我认为自然界所有的声音都是可以相互对话的。尘土和风可以对话,风牛马可以对话,万物间本是通的,写作只是找到那些秘密通道的方式之一。
北青报:回到刚才说的都市的话题,我觉得现代人身处的世界,因为声音太多了,人们不仅听不见自然还听不见彼此,大家都在吵架,所以反倒是辽阔的地方,人才能静下来听见声音的形状。
刘亮程:《诗经》时代,自然大于人类,人敬畏自然,才有了那些自然与人同在的诗歌。但这个时代社会大于人,城市大于人,人需要认真面对城市社会,需要耗费更大的精力、更多的语言去关注这个大事物。自然便被疏远了。我们也失去了书写自然的能力。
小说家的目的
是让这个世界在语言中“真实”
北青报:您这本书叫《捎话》,主人公刚好是个懂很多语言的翻译家,他在里面承担一个捎话人的作用。您也说小说家就是捎话人,文本内外这两个捎话形成了非常有趣的映照。在您看来,捎话的行为在您的创作与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作用?
刘亮程:我生活在一个多语言地区。我用汉语写作,但会好奇用其他语言的写作者他们写了什么。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,我们共同的生活,在其他语言里是一种怎样的境况?在这样的环境中,语言造成了隔阂,但也在努力沟通。
北青报:您曾经说,多一种语言,就多了一个黑夜。
刘亮程:这是我对语言的一种反思。在《捎话》中,我想呈现的不仅仅是人的语言,还有人之外万物的语言。万物的语言在《捎话》中是通的,唯有人的语言因为族群关系它是割裂的。人的语言是需要相互翻译的。小说写到最后,唯一不需要翻译的驴的叫声,成了天地间的一个原声。这个原声就是没有被磨损过,叫遍世界也不需要翻译的驴鸣,而且它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庭。
我生活的新疆,在古代这里就是一个多语言并存之地。汉代有36国,数十种语言存在于这个区域,古代四大文明带着各自的语言和宗教文化,在这里相遇。语言之间需要翻译,有时候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和误解。即使不需要翻译的同一种语言,在相互交流过程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误解。现在我们不需要捎话人这种职业了,我们点一下手指靠微信就可以把一句话传给别人,但语言的误解也处处可见。语言并不因为现代通讯的通达便捷就消弭人心间的距离。我们生活在语言中,我们创造了语言,语言又反过来统治我们。除了语言我们不能有其他交流的方式。小说家的目的是让这个世界在语言中“真实”。这种“真实”又是靠虚构完成的。《捎话》也是用那些语言书写语言的困难。
我相信不同的语言是由不同心灵构造出来的。语言是民族的密码,尤其文学作品,是一种语言更复杂的文化和情感密码。每一种语言都自带保密系统。能够翻译给另一种语言的,或许只是表层大致的意思,它的深层秘密无法翻译。汉语和英语,再怎么翻译都如隔着一个黑夜。这是不同语言间的不可言。
人与万物同构共居
建立起生命或灵魂体系
北青报:从《虚土》《凿空》到《捎话》,您的很多长篇都有超现实的处理。但《捎话》算是完全的超越虚构的一部作品。
刘亮程:应该说这是我这种写作体系体现得最完整的一部作品。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开始,到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在新疆》,我这种书写人、动物、万物的方式其实一直如此。只不过在这部作品中,我把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个体系完整呈现出来,就是人与万物同构共居,建立起生命或灵魂体系。这本书中所建构的世界的层面,从地上到天上,声音的层次、构造,还有那种人和其他事物相互交流的关系,这种设定都是以前作品中偶尔会有的。
作家的清高和孤傲
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
北青报: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看小说了,有各种各样的媒介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。您觉得和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相比,自己的读者在变多还是在变少?
刘亮程:在变多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每年的印数都在增加。《捎话》刚刚发行,销售已达数万册,它会和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一样被读者接受。就像我刚才说的,所有的文学作品可能也是一种捎话形式,作家是一个捎话人,把自己要说的话通过这样一本书,捎给更多的人。这些话可能永远都在路上,就像这本书中作为一头毛驴的那一场捎话,我并没有追求它的到达,但是话在路上走。那些要传达给另一只耳朵和另一颗心灵的话一直在路上走,小说家只是让这些话走起来,具体走到哪,接受它的心灵是谁,能不能到达这是另外的一回事。
北青报:对一个作家来说,一部作品的大获成功,会不会是一种压力?比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被大多数人知道。
刘亮程:应该不会吧。因为我的作品是渐渐被读者知道的。其实作家也不知道自己的读者在哪里。作家写一部作品,更多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,而不是为读者着想。我写作时心中是没有读者的,只有作品本身。这便是作家的清高,我觉得这种清高和孤傲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。尽管有时候出版社可以把一本书设计得花里胡哨,去讨好读者,但作家不会。一个写作者完全忘记读者他才有读者。因为读者欣赏的是作家那份清高、孤傲,而不是低下媚俗。我记得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出版之后许多读者向我表达说他喜欢那本书中的孤独,孤独恰好是读者欣赏这本书的一个理由。
北青报:这和您想象的一样吗?
刘亮程:应该是一样的。因为那种孤独就代表了作家的清高和孤傲。
北青报:您最近写作的状态本身也是孤独的吗?
刘亮程:写作状态谈不上,因为我的写作很慢,细水长流,每天写一点。这本书写了四年,时间确实很长,但是没有四年又感觉写不出来。当我开始写《捎话》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着这个故事往前走,自己带着那么多的话语往前走。我也需要长大,也需要经历书中捎话人所经历的年月,所以在这样写作中我开始觉得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写完,在写完之后我发现,这个故事变成另外一本书。我想,一本书的长成,就像一棵树的长成一样,它需要有一个年轮,这个年轮到了它自然就成形了。
北青报:听说您已经在写下一部长篇了,进展如何?
刘亮程:新作正在写,可能2019年会写完,是以《江格尔》(流传于新疆、内蒙古等地的蒙古族英雄史诗)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这几年我一直在读《江格尔》,边读边想,这部史诗诞生的那个时代,人类是如何想象这个世界的。读着读着又感到不过瘾,觉得古人的想象力是有模式的,总是想到某种程度就想不下去了。那好,我就在古人想不下去的地方继续往前想,在史诗的尽头进行无边无际的想象。
采写/本报记者 张知依



 聆听花语77432373
聆听花语77432373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