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夏天似乎比较闷热。
乌云不请自来,耀武扬威,要占领那虚空。那浓墨抹黑了天空,如同名家的水墨画。乌鸦似乎无事可做,扑棱着翅,热烈的呱呱叫。那柔弱的黑猫,此时似乎从某处醒了过来,睁着绿色的眼睛四处张望,精神抖擞的迈着轻盈的步伐。老鼠也悄悄的钻出洞,探头探脑嗅探讯息。饿的瘦骨嶙峋的,似乎很可怜。那常在蔓密的枝头清唱的杜鹃鸟,此时似乎不告而别,不见了踪影。紧迫压抑的情绪到底从心底的不知名地方冒了上来。有如此刻,我望着外面的天地,站在窗前。
窗子上似乎遗留着许多小孔,不知是何年何月谁人开凿下来的,真是有心人。风像嚣张的蝙蝠,大张着黑色的翅膀,红色的眼睛表露出嗜血的本性。它们成群结队的扑了过来,黑压压的。把百叶窗击打的啪啪响,看见我,却很高傲,轻蔑。不打一声招呼,似乎不是什么好客人,我十分不喜欢它们。白天像个乖孩子,很有礼貌。到了阴雨天来临,便到处肆意的游荡。一群有趣而又淘气的小家伙!我想它们的父母早就想好好教训一下它们了,叫你不听话!
我饶有兴趣的看着窗台那些小孔被吹得呼呼响。风刮得很猛,像充满活力的青少年从来都很叛逆,不满的情绪总是压抑不住,非得和这世界过不去,唱反调。
我看了好一会儿,不觉眯眼,转过身,肃然面对着这同样肃然的黑暗的小房间。它很小,没有什么光线透进来。总是让人觉得很局促。房梁上悬挂着一只发出暗黄色光线的白炽灯泡,上面沾满了蛛网和油腻。当然这微微的光亮是远远不能让我满意的,为此我常与说话粗野长着大胖腰的女房东吵架。她总是不屑地说:要走,请随意!我坳不过他,只好作罢。
房内潮湿的气味总是恰如其分的找到我的鼻子,固有的一声不响,被我嗅探到。它能忍受得了,可是我不能。几次萌生想搬出去的念头。然而懒惰随遇而安的习性却总是牵着我的腿,拉着我的手,不让我走。我屡次看着沉重老旧的行李箱,苦笑。
在这小屋子里唯一的植物,一盆水仙,它似乎也想苦笑。连苦笑似乎也带有一丝不明来由的清香。它静美,它顽皮,我认为。我想我的知己,在这里,就是它,水仙花。
外面有更加波澜壮阔的世界,可是我的心似乎很在意这个房间。我想它是在这里有点习惯了。
暗雨落了下来,击打着瓦片。窗外的池塘,顿时囊括了所有的涟漪。红莲经过冲刷,愈显明艳,光彩夺人。鱼儿留恋的不是浑浊的池水,想必就是那红莲了。倘若不是,却为何总是在它的旁边欢快的游走,不忍离去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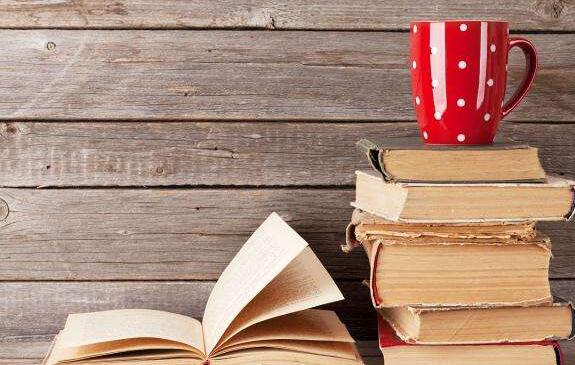







 站在坟头指挥孤魂野鬼
站在坟头指挥孤魂野鬼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