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江日报记者周劼
“中国学**”的后续
“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,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”,这话其实也适用于学术研究:现实的契机常常是学术的动力,哪怕是跟现实关系并不紧密的历史研究。比如,美国的中国学研究,1949年以前都是边缘学科,不温不火,几个老教授发发思古之幽情就完事儿了;等到中国革命成功,特别是接下来20多年(1949-1972)的中美对峙,让美国人痛定思痛,他们觉得不仅在现实中“失去了中国”,在学术上也“失去了中国”,这种失去让美国在诸多问题上碰得头破血流。举一个例子,美国越战失败,全国哀号,费正清痛斥美国国务院无能误国,他说,但凡国务院有几个中国通,美国也不至于在越南败得那么惨。越南?中国通?他的逻辑是:不了解中国,怎么理解得了越南;不知道中国革命,怎么认知得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。用他的话说:
中国革命是“一场伟大的革命,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,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之中……对历史学家来说,现在我们既然己经拐了个弯、换了种角度,那么中国过去的一切看起来也就迥然不同……
现实逼迫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转向,也掀起了称之为“中国学**”时代,这个时代从外部环境来说,要钱有钱要人有人,有人统计,1958年至1970年期间,美国联邦政府、基金会、高校共投入大约5千3百万美元用于资助中国研究。各个大学纷纷设立中国学研究机构、培养研究人员、出版研究著作、建设资料库等等。中国学成了“显学”。从内部学术理路来说,中国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:
了解中国乃是当今人类面临最紧迫的、思想上的和实践上的挑战,而且这一挑战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紧迫。
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博伊德(Julian P. Boyd)在1964年第79届年会的主席演讲中的话。
了解中国,自然越从根儿上了解越透彻,所以除了现实问题的决策性建议、报告外,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在那个时候越来越深入,越来越引人注目。他们除了对中国资料的占有外,还有西方学术的严格训练和世界历史学背景的观照,几个因素相结合,他们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。这条路被中国学者命名为“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法“:“在空间方面,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,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;而在时间方面,则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,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。简言之,从‘西’看‘中’与自‘中’视‘西’结合,同时从‘今’察‘古’和由‘前’思‘后’并行。”这种多元与多维的史学常让“身在此山中”中国学界有醍醐灌顶的醒豁之感。
”学术的**“带来中国学研究的繁荣一时,现在我们熟知的费正清、鲍大可、列文森、施坚雅、史华慈、孔飞力等中国学家都是那个时候美国中国学界的中坚,他们的著作很多现在都成了名著经典;也带来了美国中国学人才培养的有序代际。易劳逸就是费正清培养的第二代美国中国学界的中坚。
时空的双向交叉
易劳逸(Lioyd E.Eastman),生于1929年,师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国史,他也是与罗友枝、魏斐德等人并驾齐驱的顶尖汉学家,现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。其所著《毁灭的种子》(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一种)《流产的革命》等书是许多专家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案头书。
易劳逸的中国史研究最明显地体现了”从‘今’察‘古’和由‘前’思‘后’的双向交叉“。他最开始研究民国史,1980年代初的《毁灭的种子》《流产的革命》等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《毁灭的种子》研究的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垮台。而要研究垮台,就得知道它为什么上台,于是《流产的革命》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为什么从成功走向失败。而要知道失败,就得知道国民党当政时期的政治行为模式。在《流产的革命》中易劳逸得出一个结论:正是传统模式的延续及未能得到根本改造,使国民党很快蜕变,日趋腐败,不能承担完成中国现代化改造的任务,从而被历史的发展所淘汰。这个传统模式,易劳逸称之为“权威—依附”模式,中国传统社会身份取向极强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地位,而这个地位就决定了每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的行为方式。从政治的角度看,人要么处于“权威”,要么处于“依附”。“权威“与“依附”互利,依附者指望从权威者那里得到提拔和保护,权威者则需要依附者无保留的忠诚和绝对的服从,而依附者自然俯首贴耳,唯命是从,他们懂得,对一项错误的决定,与其明知其错而反对,不如让它在实行中碰得头破血流,让制定者自己纠正为好。这种唯有称是,绝不言非的行为特征,成为旧官场上下级关系的准则。下级没有主动性,也不准有主动性。“权威一依附”模式的另一个行为特征是人人都埋头于编织个人关系网,行政系统也几乎完全是靠这张关系网来运行。“人情”在关系网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与此有关,便产生了“权威一依附”模式的第三个特征,即官员们不讲原则,有令不行,为帮派私利牺牲原则。这种旧的政治行为模式本应该利用革命的手段消灭掉,但国民党不仅未能做到这一点,反而使旧的行为模式变本加厉。在易劳逸看来,国民党发动革命(推翻满清和推翻北洋军阀政府),却迅速向传统的政治行为模式靠拢,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俘虏。
这种“权威-依附”模式又是如何产生的?就是这本1980年代晚期所写的《家族、土地与祖先——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》要回答的问题: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的问题,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体制和结构。
《家族、土地与祖先》是一本可称之为“中央帝国社会学密码”的书,该书详尽地描绘出中国近世四百年社会经济变迁史,试图找出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社会密码。很多国内外研究论著当中对《家族、土地与祖先》这本书多有引用,将其当成研治中国历史的重要作品,这是首个国内译本。
常与变
易劳逸回溯了中国历史400年,他说,从晚明开始,中国社会就处于一种变革状态。人口增长和经济商品化推动了诸多的巨大变化。但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改变。这是一个巨大落差与错位的时代,也是借着改革突破自身限制的极好时机,但清朝错过了,民国也错过了,所以中国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历尽坎坷,即使到了今天,我们还在社会与文化转型中艰难前行。
”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“是中国社会行为的文化基础,这个根基如此牢固,很难改变,但又不得不改变,因为它的很多价值观和现代化是相悖的,中国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来回拉锯中动荡、发展,中国人也在这样的取舍中犹疑不安。不过,易劳逸看到了另一面:
这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就是既热情又冷漠、既勤劳又懒散、既进取又保守、既慷慨又自私的群体,应该说中国人身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,但正因为如此,他们才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着迷的居民。

《毁灭的种子——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(1937-1949)》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

《流产的革命——1927-1937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》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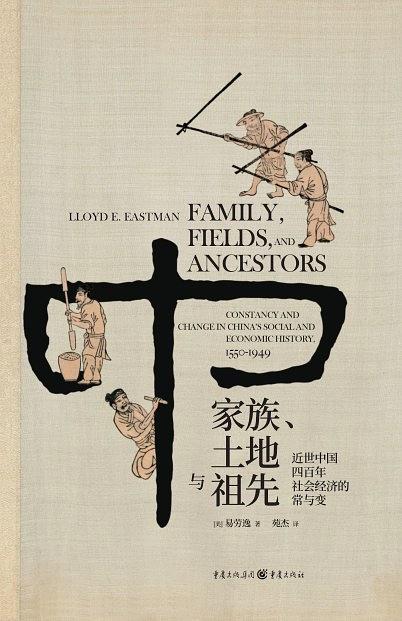
《家族、土地与祖先1550-1949——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》重庆出版社2019年



 皇冠落地徒悲伤
皇冠落地徒悲伤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