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雷文超
一个人的墓志铭,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和解读。要写好一个人的墓志铭,不仅要写清楚他的生平,更要让读者,通过墓志铭,去读懂这个人的一生。而在中国文学史上,有这样一段绚烂的佳话,从杜甫到李商隐,几代诗坛巨匠,穿越了整个大唐王朝的兴衰,在一次又一次的惺惺相惜,一次又一次的意气相投中,完成了一代人对上一代的解读和传承。
唐代宗大历五年,在贫病交加中,杜甫在耒阳走完了他潦倒困苦的一生。临终之际,杜甫遗愿归葬于首阳山,但迫于贫困,杜家子弟只能在耒阳聂令的帮助下将杜甫下葬。在有生之年,杜甫和他的诗作并没有受到什么赞许。而随着时间推移,数十年后,在白居易等人的大力倡导下,杜甫才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启蒙者而大受推崇。也正是在这时,杜甫的遗骨才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,完成了他的心愿。

归葬之时,由正被贬谪的元稹为杜甫撰写了那篇著名的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。在杜甫去世9年后才出生的元稹,并未真正经历过杜甫的人生,也从未与他交游,但却在当时“扬李抑杜”的氛围中,给了杜甫高度的评价。
盛唐继承梁齐的靡靡之音,在这个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的年代,是那么的无力和衰微。人们需要看到的、听到的,是如杜甫一般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的呐喊和呼号、是他那“人生无家别,何以为蒸黎。”的感同身受。
在经历了贬谪的困苦,也阅遍了民生之艰难后,元稹通过那一篇又一篇或悲劲激荡、或彻骨清流的诗作,和数十年前的杜甫,进行了一次超越时空、超越自我、超越了彼此经历的灵魂对话。
而在此之后,元稹的文学创作也开始了转变,作为第一个给与杜甫高度评价的人,他继承着杜甫的衣钵,开始将陷入沉寂的诗歌,引向发自肺腑的现实主义,引导着诗歌成为反映现实、呼喊民生多艰的工具。

唐文宗大和五年,人生中四度被贬的元稹在武昌去世。他的一生知己,白居易怀着巨大的悲痛,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。
元白二人的相交与相与,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璀璨佳话,贞元十九年,元白二人同时登书判拔萃科,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,因此相识,拉开了贯穿二人一生的友谊。他们一生如同伯牙子期,相互唱和,以才气相结,以风骨相与,数十年而见肝胆。
在元稹为杜甫写完墓志铭后,在元白二人的倡导下,诗坛开始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,他们并肩继承着杜甫的衣钵,针砭时弊,反映民生。希望用诗歌来唤醒昏聩的当权者,为普罗大众发声,将诗歌作为引导政治的方向。
然而,也正是因为二人诗作对于当权者的讽喻,他们开始了不断被贬的飘零人生。唐宪宗元和四年,元稹被贬江陵,四年后被召回。回到长安后,他和白居易诗酒唱和,并拟编纂《元白还往诗集》。然而,诗集尚未遍成,他就再度被贬往通州,开始了近二十年的贬谪生涯。几乎同时,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,这对知音挚友,从此开始了难得再见一面的困苦生活:“与君相遇知何处,两叶浮萍大海中。”而他们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,也在此期间遭受重击。
在这困苦之中,他们以诗文作为慰藉,以友情支撑苦难。其后数十年间,二人写下了180多首往来唱和之诗作。最为著名的,当数元稹的那首《闻乐天授江州司马》:
残灯无焰影幢幢,此夕闻君谪九江。
垂死病中惊坐起,暗风吹雨入寒窗
唐文宗大和四年,元稹再度被贬,在途中的驿站,他再度见到了白居易。二人感叹时事多艰,命运飘蓬,不由得潸然泪下。而没想,这一见,则是二人的诀别。
一年后,元稹暴亡于武昌。留给白居易的,则是钟期殁已久,世上无知音的哀叹和思念。他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:
实有心在於安人治国,致君尧舜,致身伊皋耳。抑天不与耶?将人不幸耶?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,勤而行之,则坎坷而不偶,谪瘴乡凡十年,发斑白而来归;次以权道济世,变而通之,又龃龉而不安,居相位仅三月,席不暖而罢去。通介进退,卒不获心。是以法理之用,止於修一职,不布於庶官;仁义之泽,止於惠一方,不周於四海。故公之心不足也,逢时与不逢时同,得位与不得位同,富贵与浮同。何者?时行而道未行,身遇而心不遇也。执友居易,独知其心,以泣濡翰。
这天下之大,恐怕也只有他们二人,才能明白对方的心意了。元稹死后,那个曾经关注苍生疾苦、鞭挞权贵的白居易,也彷佛随他一起而去。剩下的,则是独善其身、过着闲适生活的“香山居士。”

他为元稹写墓志铭,不仅为这位挚友的一生做了评价和解读,也像一面镜子一样,为自己曾经的过往和事业,做了一次告别和总结。
十五年后,七十五岁的白居易在洛阳溘然长逝,他死后,墓志铭由李商隐撰写。
白居易年长李商隐四十多岁,在李商隐名著于世之时,白居易已经步入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。他爱极了李商隐的诗文和才华,在醉酒之时曾戏谑说:“我死之后,能(投胎)成为你的儿子,就非常知足了。”
可是,当许多年后,因为李商隐的四处奔波,这个被李商隐取名为白老的孩子,却因为贫苦,而失去了成才的机会,变得痴痴笨笨。“渐大啼应数,长贫恐学迟。”就连温庭筠也来笑话:“以尔为乐天后身,不亦恬乎?”如果白居易泉下有知,不知是何感想。
同时,一生被晚唐政治漩涡所困扰的的李商隐,对于白居易,却是不解的。年轻时的他,必然是受乐天影响极深,也深对其认同的。如《重有感》、《曲江》等诗,无不充满了继杜甫、元白而传承来的讽喻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。然而,相比于元白等人,更加郁郁和飘零的李商隐,人生最大的主题却是悲伤和离别,我们也只能从他早年的这些作品当中,才能寻觅到那个怀匡扶国家之志向,欲回天地之心的年轻人。

而在甘露之变中,年轻的李商隐对于混乱的政局大感愤懑,提笔写下了《有感》三首,而此时的白居易,却写下了:祸福茫茫不可期的话语。这样的白居易让李商隐感到陌生,也感到悲哀,这还是那个曾经写下卖炭翁的白乐天吗?在乱世之中,他只能孤独的站着,膝盖发冷。
于是在白居易的墓志铭中,我们看到了李商隐对白居易的解读,这其中,更多的是他的迷惘:在墓志铭中,他对白居易的人生、行事,包括其忠正廉洁、直言纳谏的品格进行了高度赞扬,但对白居易的诗文成就,却只一笔带过。
也许数年后,当李商隐走向他的人生尽头,他才终于得到了答案,那就是生命,原本无题。
十二年后,李商隐病逝。而他死后,诗歌也逐渐陷入衰落。中华文化的另外一个高峰:宋词,开始登上舞台。
从杜甫到元稹,从元稹到白居易,再从白居易到李商隐,在百年跨度中,他们通过墓志铭这种特殊的方式,完成了诗歌和文化的传承。
他们的生是志同道合的相与,诗文则是风骨灵魂的传承。
这一切,正应了2000年前的庄子所说:“指穷于为薪,火传也,不知其尽也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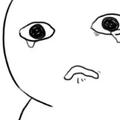 丿内涵灬费玉清
丿内涵灬费玉清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