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清朝入关以后,政治思想,可以说是消沉的时期。这(一)因异族压制,不敢开口。(二)则宋明的学风,流行数百年,方向有些改变了。学者对于(A)国家、(B)社会、(C)个人修养的问题,都有些厌倦,而尽力于事实的考据。考据是比较缺乏思想的——固然,考据家亦自有其思想,但容易限于局部,而不能通观全体。而且清朝人所讲的考据,其材料是偏于古代的,所以对于当时的问题,比较不感兴趣——如此,政治思想,自然要消沉了。
静止的物体,不加之以外力,固然不会动,但是苟加之以外力,外力而苟然达到相当的程度,也没有终于不动的。西力东侵,是中国未曾有的大变局。受了这种刺激,自然是不会不动的。所以近代政治思想的发皇,实在我们感觉着外力压迫之后。
感觉到外力压迫之后,我们的政治思想,应该怎样呢?照现在的人想起来,自然很为简单,只要舍己之短,效人之长就是了。但是天下事没有如此简单。须知西力东侵,是从古未有的变局,既然是从古未有的变局,我们感觉他,了解他,自然要相当的时间。须知凡事内因更重于外缘。同一外力,加于两个不同的物体,其所起的反应就不同,这就显得内在的力量,更较外来的为重要。所以我们在近代,遭遇了一个从古未有的变局,而使我们发生种种反应。当这种情形之下,为什么发生如此样子的反应呢?这一个问题,我们是要将内在的情形,详加探讨,然后才能作答。我们内在的情形,却是怎样呢?
第一,中国因(A)地大,(B)人多,(C)交通不便,(D)各地方风气不同,(E)社会的情形也很复杂,中央政府控制的力量有限;而行政是依赖官僚,官僚是无人监督就要作弊的;与其率作兴事,多给他以舞弊的机会,还不如将所办的事,减至最小限度的好。这是事实如此,不能不承认的。所以当中国的政治,在理论上,是只能行放任主义的;而在事实上,却亦以放任主义为常,干涉主义为变。——变态就是病态,人害了病,总是觉得蹙然不安,要想回复到健康状态的,虽然其所谓健康状态的,或者实在是病态。但是彼既认为健康状态,觉得居之而安,就虽有治病之方,转将以为厉己了。从来行干涉主义的,每为社会所厌苦,务求破坏之,回复到旧状以为快,就是这个道理。事实上,中国是只能行放任主义的,但在人们的思想上,则大不其然。
中国思想的中心,是儒家的经典,所称颂的,是封建制度完整时代。此时代的特色,是(甲)大同时代社会良好的规制,尚未尽破坏,(乙)而君主的权力也较大。人民受儒家经典的暗示,总觉得社会应该有一个相生相养、各得其宜、使民养生送死无憾的黄金时代,而此种时代,又可借政治之力以达之,所以无形之中,所责望于政府者甚深。以上所述,是老死牖下,和实际政治无甚接触,而观察力也不甚锐敏的读书人。若其不然,则其人又容易受法家的暗示。法家所取的途径,虽和儒家不同,但其所责望于君主者也大,所以有实际经验,或观察力极锐敏的政治家,对于政府的责望,也总超过其实际所能的限度。
第二,在实际上,君主专制,是行之数千年了,但在理论上,则从来没有承认君主可以专制。其在古代,本来是臣有效忠于君的义务,而民没有的。反之,如儒家所提倡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等理论,则君反有效忠于民的义务。此等思想,虽然因被治阶级之无能力,而无法使之实现,但在理论上,是从来没有被破坏过的。试看从来的治者阶级,实际虽行着虐民的事,然在口头,从来不敢承认虐民,不但不敢承认虐民,还要装出一个爱民的幌子,便可知道。立君所以为民,这种思想,既极普遍,然则为民而苟以不立君为宜,君主制度,自然可以废除。这只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。从前所以不敢说废除君主,只是狃于旧习,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,无君便要大乱;因为国不可一日无治,既要有政治,即非建立君主不可。——现在既然看见人家没有君主,也可以致治,而且其政治还较我们为良好,那么,废除君主的思想,自然要勃然而兴了。两间之物,越是被人看得无关紧要的,越没有危险。越是被人看得重要的,其危险性越大。中国的君主,在事实上是负不了什么责任的,然在理论上,则被视为最能负责任,最该负责任的人,一切事情不妥,都要归咎于他。这样的一个东西,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时,其危险性自然很大。
第三,中国人是向来没有国家观念的。中国人对所谓国家和天下,并无明确的分别。中国人最大的目的是平天下。这固然从来没有能做到,然而从来也没有能将国家和天下,定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,说我先把国家治好了,然后进而平天下。质而言之,则中国人看治国和平天下,并不是一件极大极难的事,要在长期间逐步努力进行,先达到一件,然后徐图其他的——若以为难,则治国之难,亦和平天下相去无几。总而言之,没有认为平天下比治国更难的观念。因为国就是天下,所以治国的责任,几于要到天下平而后可以算终了。这种观念,也是很普遍的。世界上有哪一种人,哪一块地方,可以排斥于我们的国家以外,(A)我们对于他,可以不负责任,(B)我们要消灭他们以为快,这种思想,中国人是向来没有的。中国人总愿意与天下之人,同进于大道,同臻于乐利。有什么办法,可以使天下的人,同进于大道,同臻于乐利,中国人总欣然接受。
第四,确实,在从前也没有一个真正可称为国家的团体,和中国对立。但是和中国对立的团体,就真个没有了吗?这个自然也不是的。这个对立的团体,却是什么呢?那与其说是国家,无宁说是民族。本来国家是一个自卫的团体。我们为什么不和他们合一,而要分张角立,各结一团体,以谋自卫呢?这个自然也有其原因。原因最大的是什么?自然要说是文化,文化就是民族的成因了。中国所谓平天下,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同化之,使之俱进于大道。——因为中国人认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的——所以和别个民族,纷争角立,是中国人所没有的思想。但在事实上,(A)他们肯和我们同化,自然是最好的。(B)如其不能,而彼此各率其性,各过各的安稳日子,那也不必说他。(C)他要来侵犯我们,那就有些不可恕了。(D)他竟要征服我们,那就更其不可恕了。理论上,中国人虽愿与天下各民族,共进于大道,但在事实上则未能。不但未能,而且还屡受异民族的迫害,甚而至于被其所征服。这自然也有激起我们反抗思想的可能,虽然如此,中国人却也没有因异民族的迫害,而放弃其世界大同的思想。中国人和人家纷争角立,只是以人家欲加迫害于我时为限。如其不然,中国人仍愿与世界上人,共进于大道,共臻于乐利;压服他人,羧削他人,甚而至于消灭他人的思想,中国人是迄今没有的。
由第一,所以有开明专制的思想,这是变法维新的根源。由第二,所以民主的思想,易于灌输。由第三,所以中国人容易接受社会主义。由第四,所以民族主义,渐次发生。
这是近代政治思想的背景。
摘自《吕思勉史学经典·中国政治思想史》
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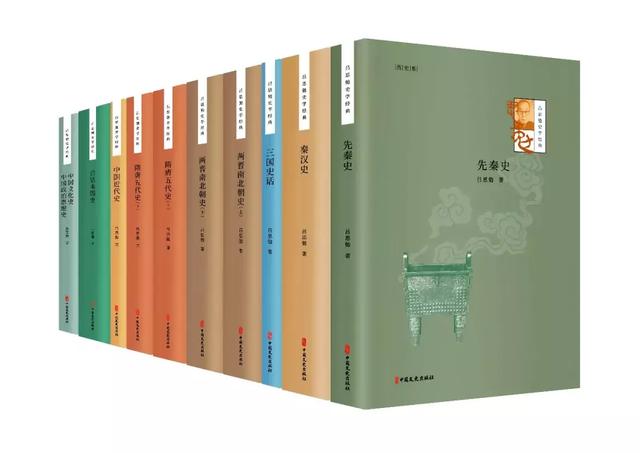



 13907975191
13907975191

